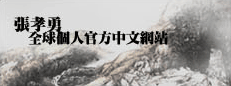徐冬青:艺术是一种尊重
艺术不是仰视,是一种尊重”——与女艺术家徐冬青的一次对话
记者: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去了,现在是2011年的第二天,2010年岁末每个媒体都会做年终盘点总结,就是把去年国内发生及有影响力的事件进行了新角度的讨论。不知在这个时刻你在做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新年?
徐冬青:我感觉那个新旧交替的片刻很静。我当时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腿上放了本泰戈尔的书在读。我是读着泰戈尔的诗迎接的2011年,内心感到无比安宁。
刚过12点,我心里一动:2011年来了。所以在2011年的最初时刻,我给朋友发了短信说:“2011年了,好新啊!”
记者:有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准备来迎接?
徐冬青:没有刻意准备,一切就是那样自然地发生着,每一年都不同,该怎样就怎样了。但我确实发觉,现在和以前相比我的庆祝方式发生了变化。
记者:以前会怎样庆祝?
徐冬青:以前我会扎到人堆里和人们一起狂欢,而现在我更愿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度过,仿佛我觉得如果声音太大就会把这种喜悦给吓跑了似的。
记者:其实我注意到你,是觉得你是个有着内心世界的艺术家,也比较喜欢独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和大家一起用比较High的形式欢庆节日转变到现在这种状态?
徐冬青:应该是从2008年开始的。
记者:是经历了什么事吗?
徐冬青:实际上还是和画有关系,有一段时间我几乎画不了画了。
记者:为什么呢?
徐冬青:后来想是因为当时把自己当成一个专业人员来对待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画家?
徐冬青:那倒没有,只是给自己施压、强迫自己了。
记者:有一段时间是你不情愿画画的?
徐冬青:小时候画画是出于喜爱才去画的,那时每当手拿画笔、轻轻触摸画纸的时候心里都会莫名地激动,有一种新鲜感,后来长大进入院校接受了专业教育,再到真正地进入中国国家画院这种专业单位以后,需要参加的展览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也得画,再加上有些展览还要经过评选,无形中在不自觉的时候又有了比的心态。可你知道的,艺术又不是体育竟赛,它应该像花开花落一样地自然,心中有情自然有感而发,人在紧张的状态之下就不容易有灵感,所以一旦抱有这种比的心态去画画,其实就偏离了艺术之路。
好在这个时候我停了下来不画了,那时我经常会问身边画家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画画?”这种寻找答案的过程差不多持续到2008年初,春节之后我开始恢复,感到自己的内心又有新的东西涌溢出来。恢复以后我画的第一张画是《远方的消息》。
记者:是不是在你画室看到的那张画得密密麻麻的大画,感觉信息量很大,画了多长时间?
徐冬青:用了4个半月的时间画完的。现在再看这张画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当时怎么那么不怕麻烦画了张如此密集的画。也许是因为一个人长时间不说话,需要表达的太多了,所以才画成了这样一张画。
从《远方的消息》动笔开始我重返艺术之路,也就是从那年开始,我庆祝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我现在表述的语言发生了变化,更愿意以画画的方式去表达,而不是用嘴巴去说,如今我很享受这样坐在安宁之中、缄默的庆祝,独自体验内心感应到的一切。
记者:当你在陷于创作困境阶段,一张都没画吗?
徐冬青:也有一朵两朵的花开,但是很少,自己又觉得不是。
记者: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的话,你说的不是,是指专业方面像权威学术认定标准的界定,还是你觉得跟你内心想追求的东西有一点远。
徐冬青:是当时没有感觉,现在想想,其实困惑也是一种感觉。或者是因为自己不自信了,因为你受过多年的专业训练,手也会存有记忆,随手就可以画出几个图形或几张画,但自己心里觉得太表面,甚至有些言不由衷,现在看也不是这样,那时候画的是那时候的自己。我在寻找,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
记者:处于那段时间的状态是比较纠结吗?
徐冬青:很纠结,那段时间里画画对我成了一件痛苦的事,画画的喜悦消失了,我甚至愤然将画笔摔在地上,第二天跑去爬香山。但其实这个阶段是必经的,省略不掉。
记者:去年10月份你同其他的艺术家在马奈艺术空间做过一个展览,其中展出了你在2006年画的《物影》系列作品,也就是你们专业人士最认可的屏风系列,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感觉,不知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画的这些画?
徐冬青:在《物影》系列之前,我画的大都是陪伴在我身边的室内的一些景物,但是到了2005年底的时候我的人生好像又到了一个底端,状态非常糟糕,老是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没有光亮的黑窟窿里,我当时心灰意冷失去了勇气,感觉也没有力气再爬起来,在这个关口我一个人去了云南,去了云南的西双版纳,那里的阳光照亮了我心里希望的种子,大自然柔软了我的心,奇迹像神话般降临了,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所有经历的一切都太真实了,不是梦。早晨一醒来,拉开窗帘,大自然的美色就“呼啦”一声扑面而来,像戏台上的大幕被拉开一样。别人感觉是梦,可能是因为觉得在现实世界里它们都不存在了。我从云南回到北京之后,当时心里仍然很激动,感觉自己从南方衔来了一堆花花草草,想画,一时却又不知如何摆放,就先写了一些文字,就是那篇《在西双版纳等你》,这个“等你”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等我”。 之后就画了《物影》这个系列。所以当时屏风这种形式,是因为需要才出来的。
记者:为什么现在又不画了呢?
徐冬青:现在不需要了。因为现在我再画它们的时候,我感觉不同了。它们本身就穿过时间了。
记者:你认为想做艺术家和你真正成为艺术家之间是否有一段心理转换和过渡期?
徐冬青:你说的成为真正艺术家的心理转换,我个人认为自我确认最重要。这种心理转换和过渡期可以认为是他(她)的再一次觉醒,艺术本身就是他(她)的生活。意识到这点后,我就踏实了。
记者:后来你的作品找到了出口,找到了你认为是的状态时,这前后两个时间段的作品从风格或者是技法、图式上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徐冬青:有变化,修饰少了。
记者:大家对你变化后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很受好评?
徐冬青:没有,刚开始大家反而不习惯。其实都是一样的,以前的屏风系列刚开始画的时候,也不是像现在大家这么认可。作品可能都得经历时间。
记者:绘画首先是视觉艺术,当然在视觉、形式、构图上更吸引人的眼球。
徐冬青:是的,形式是很重要的,我也表述不好这种变化。其实是我更注意形式了。只不过这种形,是事物本身的形,现在画每一笔的时候都有感觉。有什么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好像更理解、更知道它们了。这种体验是不可言喻的。艺术本身内在的生长,自然而然很多东西就去除了。然而内力的增长是需要时间的,没有那么快,急不得,就像女孩子真正的美是那种从内到外都散发光的天然美,很稀有。因为真的毕竟少,所以也最珍贵。
记者:你觉得你是个当代艺术家吗?
徐冬青:当然是啦。你是怎么界定当代艺术的?现在一说当代艺术好像是有某种图式。
记者:我觉得当代艺术其实真的很难完全去界定,我所理解的当代艺术是和这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社会现象和心理状态发生关系的都是当代艺术,但是并不在于它所表现的是木雕、装置艺术、水墨等,重要的是揭示这个时代问题或者是当下的精神状态的,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文艺评论等都有关,不仅仅表现在绘画上,她更需要在理论上、传媒的介入,反照作品的关系。你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呢?
徐冬青:我理解的当代艺术应该是指生活在当代的艺术家在当时的情形下用自己的语言说出的真实的话,形式是自身产生的。
记者:现在无论是艺术界,还是社会上的其他领域都希望把自己划分为某个群体里面的,比如说我是新贵阶层,工人阶层,我在艺术里面属于当代艺术家,我是属于画院的顶级画师等,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寻找一个身份认同,都需要一个归属感。
徐冬青:那你觉得我是哪个阶层的?
记者:你可能不太去想把自己归为哪一类。
徐冬青:虽然我现在中国国家画院,可我感觉自己哪个圈的都不属于。我不是不想归,以前我也挣扎过,曾试着将自己归类,但现在这种想法我放弃了。
记者:你是独立艺术家,但是当你认识一个新朋友递名片的时候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徐冬青:我没有名片。
记者:太自信了?
徐冬青:实际上就像前面我所说的,艺术家是通过他的作品来发言的,和身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也不再想要将自己纳入某个圈子,那样的话就可能真的会被圈住而失去自由。
记者:我觉得好的艺术家是不需要一定把自己归为哪一类定为成功的标准,一定是要靠你特有的、想表达的真实感受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作品去说话。我经常看国外的展览,和别人交流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共识是好的艺术家不在于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通过什么媒介。你创作的作品,你发出的声音能反映出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的问题,你就是最牛的艺术家。
徐冬青:是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艺术是自然心性的一部分,遵循的是生命法则,艺术无国界,也不是当下能归结的。
记者: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社会属性不重要,你更多觉得你作品对你心灵的成长或者是给你的寄托更大,你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不快?
徐冬青:艺术能慰藉人的心灵,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接受教育。如果一个人处于创造之中,处在你的艺术世界里,对其他的那种伤害就不是太敏感,就像别人在暗地里向你挥舞拳头你压根就没看见,因为你的心思和注意力在别处,还有画画的喜悦也会冲淡一些愁闷。其实没有绝对的坏人,只不过是人身上有一些社会习气,程度不同罢了。
记者:你一直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吗?
徐冬青:怎么可能呢,毕竟是一个真实的人,每个人都有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我也常常陷于困境,会有危险,也会有被摧跨的时候。我失望过,但从没有真正的绝望,仿佛艺术家的作品能使自己得救。
记者:这里有一个问题,和你的专业有关,就是关于工笔画的问题。画工笔画很费时间,你为什么选择画工笔画?
徐冬青: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知道的,艺术家选择语言是出于表达的需要,我画工笔画,是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这种语言才能充分表达我的心意。你说的是实情,画工笔画的人不多,画一张工笔画确实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没有对工笔画足够的爱很难坚持下去。因为爱,所以我是心甘情愿地归顺,心甘情愿地受苦受累,但同时我获得的那种快乐也是无可替代的。
记者:据我了解在国内工笔画从发展上来说面临着一种困境或者是瓶颈时期。
徐冬青: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
记者:在具有能代表权势、政治的大型展览,大家都会说工笔画是有点匠气、狭隘、自我的小空间,过时了。你觉得目前工笔画在国内这个领域里面遇到了哪些问题吗?
徐冬青:在艺术上所有画种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不单是工笔。绘画是语言本身在表达,我们不能对语言本身作出当代或过时的判断。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理解上出了问题。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表达的形式和题材,而主要与艺术家的精神内涵紧密相连,真正的艺术是活着的东西,是活着的形式的问题,艺术本身没有固定,只不过是人的习惯固定了它。
记者:在我了解的范围内,讨论工笔画的会议和展览的人越来越少,是不是?它好像越来越变成一个非常小的群体的人在做的事。对于工笔画的未来你是怎么看的?
徐冬青:提到工笔画的未来我们倒是可以从工笔画的最初时光谈起,在原始时期,东西方文化还没有形成各自文化特性的时候,人类的文化是非常近似的,原始时期世界上的岩画艺术基本上都是采用以线描绘、平面造型的方法,这应该是工笔画的最初形态,现在大家习惯上认为的工笔画只是人们理解上的问题。正因为这种原始,所以它才更接近人类最初的梦,也更具有原动力,这样的能量将是无限的。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美术史,工笔画不会像每一个时代新出现的画种那么的热闹,但是它的发展脉络从来就没有断过,只不过是有时浮在水面有时又潜入深处。另外,工笔画的语言容量非常大,跟随时代的发展,它仍然具有强大的再生生命力。
记者:那你特别害怕创作力干枯吗?
徐冬青:我害怕固定,我画屏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他们认为我终于成熟了,好象要有风格了。当时一说我就意识到危险了,屏风这种形式绝对不能成为我的风格,或者是他们认为的风格。我不想把自己固定死。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这和你转型有关。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人,包括他的穿衣风格、作品风格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出现,突然改变的话会觉得不是他了。就像歌星的成功一定要靠着几首主打歌。当艺术家去转型的时候通常会需要做一定的心理准备,相对成功的艺术家或者有一群人来买你的东西的时候,有一定市场基础的时候,你想转型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方面的阻力。有来自外界、也有来自内部的。艺术家最重要的一定不仅仅在于他有即有的成功作品,他需要有新的创造力,有新的养分。
徐冬青:这个问题每个艺术家也不相同,有的人可能很早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语言,有的人可能在属于自己生命的各个阶段使用最为贴切的语言,因为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就如人的性格各不相同。
记者:你觉得你的职业到底能为人们做什么?
徐冬青:如果别人看到我的画,能有片刻的安宁,或者甜美地睡一觉,我就感到心满意足。美和希望永远都在。要相信爱,这很重要。
记者:你希望你的作品影响到哪个群体,哪类人?
徐冬青:普通人。有共通感受的人。作为艺术家来说总是希望他(她)的作品能再长久些,我希望我的画被挂起来所有人都能看到,而不是说被某个收藏家卷起来放在他的仓库里,或者被当做礼品送给哪个高官,送给高官就意味着会消失,我愿意被挂起来。但是,作品一旦产生以后,它就有它自己的命运。原来我每卖一张画的时候,我都会难过,都要看画很长时间,我觉得它要离开我了,但我现在就没有这样了。你完成了,至于它,会有它的命运。
记者:你觉得学艺术很难吗?
徐冬青: 艺术不是枯燥的,莫测高深的东西大家都想逃。一说就天人合一,一说学中国画就是先练几年毛笔字。搞那么难,会把年轻人吓跑的。年轻人不能接受的东西就很难再延续下去,什么东西一保护就完了。艺术不难,是一种直接的打动。艺术不是一种仰视,是一种尊重。
艺术没有国界,也不分年龄。
热门推荐
-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 2009年11月18日
- ·青妙手聚香江 绘尽锦绣庆回归 2009年11月18日
- ·南昌画派闪耀璀璨光芒 2009年11月18日
- ·香港文联主席张孝勇先生应国防大 2009年11月18日
- ·張孝勇 山水人物 可貴者膽 2009年11月18日
Copyright @ 2000-2009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京ICP备09103078号
北京联络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8号嘉华世纪C座805室 邮编:100000 电话:010-65157535
联系地址:香港湾仔打道50号马来西亚大厦1602室 联系电话:00852-51015163 00852-28346483 传真:00852-28930602/35520288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信箱 E-mail:hk_wenli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