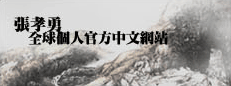汪建伟谈实验与剧场艺术:先锋是一种本性
《用赝品等待》布置了几个被切割的空间。
他是第一个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艺术家,被西方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录像多媒体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就是汪建伟。近日,汪建伟目前国内最大个展“黄灯”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亮起”。
对于自己在艺术创作领域内不断地拓宽实验边界,汪建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先锋是人的本性,而自己只是一名实验者,是一个犯错误的人。
【黄灯亮起】 对世界保持警惕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大展厅内,观众通过1.9米的通道穿行于不同屏幕之间,游离在开会者的无聊,打乒乓球者不寻常的打法之间。汪建伟有创作“黄灯”的念头,来自20世纪初一位华人发明黄灯的初衷。在美国有一次要过马路,这个发明者突然被车险些撞死,“他觉得红灯一灭就是绿灯,在中间应该有一个过渡,于是就产生了黄灯这个概念。”
“黄灯”是一种征兆,让事物总是处于允许和禁止之间。这种哲学逻辑,让汪建伟特别着迷,于是有了此次的多媒体展示。这一次,汪建伟更是玩起了戏剧化效果,将整场展览分成四幕,分在四个时间段展出。这便意味,观众要真正了解汪建伟的“黄灯”讲了什么,至少要去展厅四次。这回汪建伟玩得有点不寻常了。事实上,这不是汪的第一次。从绘画到装置再到多媒体戏剧,当代艺术的门类他统统演习一遍。对此,汪建伟则自称“自己只是一名实验者。”
1987年,汪建伟依靠当兵时画地图的技术,考入浙江美院油画系,且成为“伤痕美术”的代表画家之一。他的成名作《亲爱的妈妈》在官方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了金奖。然而,他并不满足在体制内获得的荣誉与认可,进一步尝试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绘画。
此后,汪建伟并没有在架上绘画上前行。1990年,汪建伟做出一个让业界诧异的举动――搁置画架,转向装置、观念摄影、视频等更广泛的艺术领域,“就像当初我绘画、做装置、做多媒介,所有的一切,都在于我对一个已经存在了的,被确信无疑的世界随时保持警惕。”
【剧场打开】 在美术馆里表演
就在这种“警惕”之下,1992年,他用医用玻璃器皿、输液管等器具创作了《文件》,这是汪由绘画向多种艺术形式迈出的关键一步。
1994年,汪建伟又做了著名的实验性作品《循环种植》。他回到自己插队的地方,用新品种小麦种子,与当地农民签了一协议:农民拿出一亩地做实验田,由他提供种子的来源,农民负责播种,风险与收益则由双方共同承担。汪建伟将整个过程跟踪拍摄下来,也视为自己的艺术作品。两年后,汪建伟又创作了录像作品《生产》,他也凭借这部作品参加了德国卡塞尔“第十届文献展”。
2000年,在实验的道路上汪建伟继续前行,他又开始尝试多媒体剧场,试图寻找突破现场表演与视频艺术的边界。他以个人视角重新观看《韩熙载夜宴图》,创作了多媒体戏剧《屏风》。
在那之后,剧场就成为汪建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009年,汪建伟在“时间・剧场・展览”中彻底玩了一回混搭艺术,表演、影像、装置艺术轮番上阵,观众犹如在小剧场中看了一回展览,又如在美术馆中看了一场表演。而此番,汪建伟又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内给我们亮起了“黄灯”。
对于自己这些年在当代艺术上的不断实验,汪建伟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让人记住的是:“我就是汪建伟,而不要加上前卫、先锋、多媒体艺术家等等头衔”,“所以我愿意从最简单的方式直接到我――汪建伟,把前面的定语全部删掉。”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 对话
我就是一个犯错误的人
新京报:从绘画到装置、观念摄影再到多媒体戏剧,这些年你游走于艺术的不同门类,是什么驱使你不断跨界,进行各类实验?
汪建伟:我很少说跨界这个词。跨界是外界给我的。我觉得如果去了解一个真正的世界,你就会觉得我们任何人只是处于此时此刻的自有知识系统里,并不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其他位置就变得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界在哪儿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为什么不使用跨界呢?就是(因为)它特别使人容易产生一种感觉,比如说一个演员去当导演,一个电影导演去当戏剧导演,一个摄影师最后成为一个演员。我理解这是跨行。跨界解决的问题是任何一个界在自己的封闭系统里都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它必须要交叉,这个就是真正的跨界。
新京报:你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性艺术创作,艺术界对你的评价也一直冠以先锋等头衔。
汪建伟:我觉得先锋是人的本性。你研究整个人类,(就会发现)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先锋的概念,我们承认先锋就是(因为)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要超越现在的事情。我就是干了一个人本性应该干的工作,它没有任何道德优势。我其实就是一个犯错误的人。你认为这个事情有某种可能性,但事实上,有可能性的事情就包含了错误。正确来自何处?把已经有了的东西再做一遍就有一个标准,就能以此评判你做对还是做错。我倒是觉得必须要承认艺术家的工作就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工作,它既没有炫耀你的勇气,同时也没有掩盖你这个工作还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新京报:从2000年你开始尝试多媒体戏剧一直到现在,有没有觉得将戏剧引入当代艺术中会使得表达更特别?
汪建伟:我愿意把戏剧说成剧场。它有两个意思。首先很多观点认为当代艺术就应该发生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及让正确的人、正确地观看。但是实际这个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当代艺术只能在正确的美术馆展示?我觉得这样的实验可不可以直接放到我们说的公共空间?剧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剧场实际上是一种场所。就一个场所来讲,它既然可以建造成我们认为的剧场,同时它还能做一点其他什么呢?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装置、多媒体实验作品的收藏在国内不乐观的局面?
汪建伟:中国前一个阶段完成了公众认为的艺术是可以作为收藏的观念普及,但是这个收藏大多数是跟一些传统媒介,如绘画、雕塑等有关。收藏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它从艺术之外来认可你的价值。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仅仅活在艺术里,我们也有一个艺术之外的世界。所以收藏就扩大了这个社会对你当代艺术工作本身的理解。从这个层面来讲,收藏就是当代艺术。收藏是(因为)收藏者认为艺术品有价值。他收藏的是价值、勇气和创新。通过收藏,他就把这个价值给公众传达出来,而艺术家也得到了这样一种鼓励,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持续性的东西。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简单地把收藏家一脚踹到有钱的概念上去。实际上收藏家是属于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他涉及到价值判断,否则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热门推荐
-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 2009年11月18日
- ·青妙手聚香江 绘尽锦绣庆回归 2009年11月18日
- ·南昌画派闪耀璀璨光芒 2009年11月18日
- ·香港文联主席张孝勇先生应国防大 2009年11月18日
- ·張孝勇 山水人物 可貴者膽 2009年11月18日
Copyright @ 2000-2009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京ICP备09103078号
北京联络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8号嘉华世纪C座805室 邮编:100000 电话:010-65157535
联系地址:香港湾仔打道50号马来西亚大厦1602室 联系电话:00852-51015163 00852-28346483 传真:00852-28930602/35520288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信箱 E-mail:hk_wenli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