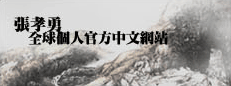方力钧 艺术圈不存在澳门赌盘机
方力钧这几年的作品一直在尝试突破“光头”符号。
新京报: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方力钧:人已经形成(对作品的)想象力和理解,就很难改变。其实这对自己也是很好的事情,让你知道观众看作品会有什么可能性。它可以让你工作的基准和考虑语言时的方式,都做出改变。就光头形象来说,我是非常大的受益者,尤其是早期时,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就没有那么多人能记住你或获得机会。从这方面来讲我应该是知足的。
另外一个就是权利。既然一个艺术家能够创造出这样的艺术符号,那他完全可以有权利从这种语言符号里去榨取最多的利润,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那么这种权利,我始终是可以保留的。我是不是使用这种权利是我自己的意愿。这不是别人说两句为什么重复,就可以左右艺术家的。其实在我们历史上,有些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在晚年或成功的时候受到了非常多的责难,类似安格尔、贝多芬,他们的处境很糟糕。很多人去攻击他没有创新、保守。但过了那个时代后,我们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中,他们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是最了不起的天才。我们在世时,并不是所有的责难都是对的,并不是说有人能指出别人的缺点,他就是伟大的。
新京报:保留光头符号是你的一种权利,但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你也在画一些长出头发或者根本就没有人的形象的作品,这是专门为了改变成见的新作?
方力钧:艺术家其实是很无奈的。更多的人不管你做了什么,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看作品。他去看展览,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既有的想象是成立的,而不是将自己腾空,去认真地解读你的作品。
新京报:这不是很悲哀吗?
方力钧:人的生命中,这种悲哀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你只要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就可以从容地去面对它了。
把作品卖给公共美术馆让更多人看
【名利】 有成功策略吗?
把作品卖给公共美术馆让更多人看
新京报:你说自己年轻时水和光头都是你想要表达的元素,但觉得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首要的还是先做一个比较强烈的视觉效果的作品为妙,就把工作顺序先安排在光头这一部分,等以后别人知道你名字,你的名字足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了,然后你翻过头来画这些视觉不那么强烈的。
方力钧:除了理想之外,你必须要考虑到理想实现的可能性。这个理想是否是你的终极目标,你这步理想和终极目标有没有障碍?就是在上厕所时,都要考虑是否需要先准备卫生纸。你看生活中的小事都需要这样安排,那面对那么大的事业,更要有条不紊地安排。你做事业时,必须这样去安排程序。这对我来讲,是最正常不过的。
新京报:这种对创作怎样的视觉符号才能成名的感悟是你当时就有的,还是后来总结的?
方力钧: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是遗传还是社会的潜移默化。其实这也是我做这个展览的兴趣之一。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候并不像你已经做过的事情那样清晰,大部分你能看到的都是结果。
新京报:当时在圆明园,你并没有把作品卖给私人。你当时有个解释是说通过卖作品,自己会有一种依赖性,一旦生活有点窘迫就拿去卖作品,不能专注于创作。但同时我看到另外一种效果,就是第一次西方展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由于你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出售,你展出的作品是最多的,西方对你的印象更深。这个效果是你当时就考虑到了吗?
方力钧:第一,当时卖作品很困难,卖作品的可能性很小。我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那个素描作品,大概有七八拨人来谈。我说一件作品三百美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件作品太贵了,都跟你谈价钱。你必须在你一时的困难和让你一辈子困难之间做一个选择。一时困难我能忍受的话,我可能是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个好的铺垫,就有一定的主动性。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另外,当时在北京,整个社会气氛非常压抑。对此我也有一些判断。我想,人类历史中,可能就是在最最灾难的时候,人民不可能长期这样哀叹,长期地灰头土脸的,他自己一定要笑起来。
此外,政府也不会让人民长期灰头土脸,愁眉苦脸地生活。它一定要想办法让人民感觉有一些空间,有一些清新的空气,然后让人民像正常的生命一样活跃起来。所以,我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觉得大概有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展览会多起来,交流会多起来,然后机会也会多起来。那时,就会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展现给世界看。
那么,后来的发展基本上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在两年到三年时间里整个形势全变了。
新京报:你这么精准的判断是跟你喜欢看历史书有关吗?
方力钧:我觉得我自己的判断一般就通过比较。拿不准的时候,我基本上是靠着生理上的判断。这是作为一个个体,最本能的直觉。你会发现你的本能判断往往是最准确的。
新京报:一开始,你的作品先被专业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然后再流通到艺术市场,这也是你对艺术家如何获得成功的策略吗?
方力钧:你必须要考虑到效率,什么是最有效的。在同样的时间里面,我可以用低于我卖给私人藏家收入的好多倍,把作品卖给公共美术馆,而其他人为了中间的差价卖给私人。区别其实已经显现出来了。在美术馆,每年有上万人,或者说有很多重要的人能够看到这个作品。但为了多得钱卖给私人,私人把那个东西放在库房里,他可能永远不再借出来,永远没有人再看到它了,它的效率就完全没有了。
新京报:那现在,同一幅作品,按照你的效率原则,你会卖给博物馆还是藏家?当然博物馆还是可能会低于藏家。
方力钧:现在我们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价格标准,所以这个根本不是我来发愁,我要想的事情了。
新京报:感觉你是很懂经营、很懂成功策略的人?
方力钧:我不知道是本能、天性,还是后天的学习。
【未来】 艺术史地位?
有好作品就一定有好收获
新京报:有些艺术家可能会觉得市场的那个卖价即使很好,也并不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也会在乎在美术史上的地位,那你呢?
方力钧:艺术是有很多种价值指标的。市场价值是艺术价值重要的指标之一,尤其是在现在。但市场价值并不是全部,还有更重要的价值指标不是用货币来体现的。
我们都知道货币是最不可靠的。如果我们把这么虚的,这么不可靠的东西放到艺术价值的最上面,囊括了艺术品的所有价值,就太不靠谱了。
新京报:中国当代艺术经历过经济危机后,很多人都说它回暖了,复苏了,那么你的判断是怎样呢?
方力钧:当代艺术品最火爆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朋友经常会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的想法是,火爆的时候是个非常态,而金融危机之后它是一个常态。
现在,我们回到常态里,我觉得挺好的。我们没有必要非要大家陷在一个非常态的情况里面,然后,或者是人高兴得疯了,或者不高兴得疯了。
新京报:你曾说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一个进行时,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艺术家到底是谁,谁都不能做出判断。你在中国当代艺术生态里,除了创作了光头这样的成功符号外,对这个艺术生态是如何运转的都很懂行。那你觉得,你会是最后留下来的这一批人吗?
方力钧:我自己始终认为,大家更加看重的是艺术创作之后的收获,它是一个附加值。我把我的精力全部用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作品上,那么它的附加值自然就提高了。跟我合作过的,比如说画廊也好,策展人也好,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非常乐观的,它们马上快倒闭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其实这都是一个附加值,我们有好的作品,就一定有好的收获。结果基本上都被我说中了。
新京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30年,你们那一代还是很占垄断地位的,感觉现在新生代爆发进而受全民关注的并不多。比你年轻的艺术家中,有你看好的吗?
方力钧:我们做这个展览的意思很明显。艺术圈不存在一个类似澳门赌盘机,能赌一下就成功的艺术家,尤其是重要的艺术家。在文化领域,尤其在艺术方面,它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艺术家这个职业必须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和长期的表现。我之所以做这样的文献展览,就是因为还没有定型,我需要更多的积累,需要更多的总结。那么更年轻的艺术家,我想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能是把每一步的工作做好,然后等到他有资历去总结过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每一步都是认真严肃的,每一步都是有成效的。
热门推荐
-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 2009年11月18日
- ·青妙手聚香江 绘尽锦绣庆回归 2009年11月18日
- ·南昌画派闪耀璀璨光芒 2009年11月18日
- ·香港文联主席张孝勇先生应国防大 2009年11月18日
- ·張孝勇 山水人物 可貴者膽 2009年11月18日
Copyright @ 2000-2009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京ICP备09103078号
北京联络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8号嘉华世纪C座805室 邮编:100000 电话:010-65157535
联系地址:香港湾仔打道50号马来西亚大厦1602室 联系电话:00852-51015163 00852-28346483 传真:00852-28930602/35520288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信箱 E-mail:hk_wenlian@163.com